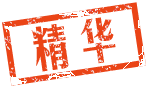|
|
一、引言
近些年来,关于中国移民史的基本史实,学术界出现了相当强大的质疑之风。最初的质疑来源于华南。他们的研究表明,在珠江三角洲地区,“许多本地人迁徙的历史传说是值得质疑的”,这些自称是宋代经南雄“珠玑巷”南下的汉人,其实是当地的土著居民,甚至有上岸的水上“蛋民”。他们通过修筑祠堂,编纂族谱,伪造族源,将自己贴上汉人的标记,不过是为了在珠江口沙田的争夺中获得有利地位的一种策略。[1]
从珠江三角洲出发,学者们开始质疑其他地区的移民传说。例如,赵世瑜在基本肯定移民史实的前提下,从墓碑与族谱中找到若干条证据,证明与山西洪洞“大槐树”相关联的移民传说,“和移民本身是两个完全可以不相干的独立部分”,并且,“传说的文本并不是在一个时间里形成的, 它们经历了一个丰富、添加、黏附的过程”。[2]也就是说,遍布华北大地的“大槐树”移民传说,在很大程度上带有虚构的成份。
与“大槐树”相关联的移民虚构,可以从民国《获嘉县志》卷八《氏族》中找到更为细致的说明:
而中原大地, 则以异类逼处, 华族衰微, 中更元明末世, 播窜流离,族谱俱付兵燹。直至清代中叶, 户口渐繁, 人始讲敬宗收族之谊, 而传世已远, 祖宗渊源名字多已湮没, 独有洪洞迁民之说, 尚熟于人口, 遂至上世莫考者, 无论为土著, 为军籍,概曰迁自洪洞焉。
所谓“异类逼处,华族衰微”,令赵世瑜“想到女真人和蒙古人在淮河以北的生活”,明代初年的华北,有点“像魏晋南北朝那样的一个族群混杂的时代”;“明朝在重新确立汉族正统的过程中,对蒙古等北方少数民族采取了鄙夷、甚至压制的态度”。因此,相当多的女真或者蒙古人,就有了“一种寻根的需求”。淮河以北的“大槐树”传说就是这样创造出来的。
在中国移民史上,与“大槐树”同时代的移民传说,还有许多。 例如,在苏北地区,有“苏州阊门”移民传说;在安徽及鄂东地区,有江西鄱阳“瓦屑坝”移民传说;在皖西丘陵,有山东“枣林庄”移民传说,在荆湖平原,有江西南昌“筷子巷”的移民传说,在四川,则有“麻城孝感乡”移民传说。以我们目前的知识,江淮之间乃至四川并不是“异类逼处”之区。这一区域不存在汉夷关系的紧张。由此看来,有关“大槐树”的理论新解,并不适用于“瓦屑坝”及其他移民传说。
除此之外,关于“大槐树”移民传说的“大批制造”,赵世瑜的解释是这样的:清末民初,中国有了亡国灭种的威胁,近代“民族国家”概念也开始传入中国, 一些地方的知识精英开始利用自己手中的文化权力, 对传统的资源加以改造, “他们希望把大槐树从一个老家的或中原汉族的象征,改造成为一个国族的(national)象征”。这些传说的广泛传布,“一定与”清代中叶以后“知识精英的推波助澜有关”。
然而,以“瓦屑坝”移民传说作为对照,这一看似合理的解释也不能成立。在另外两篇文章中,我们已经证明,“瓦屑坝”移民传说的“大批制造”,恰恰是在康熙年间甚至更早,而不是清代中叶及其以后。移民后代寻访“瓦屑坝”,也发生在清代中叶以前,而不是以后。围绕“瓦屑坝”移民传说,虽然地方精英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与“种族认同”与“国族认同”毫无关系。[3]
于是,本文的讨论,不再针对与“大槐树”相关联的理论展开,而专注于传说背后的制度与史实。赵世瑜指出,尽管存在宗族来源的大量虚构,“但是, 这并不等于说所有记载其祖先来自山西洪洞的族谱在这一点上都是虚构的, 也还有很多族谱记载其祖先来自山西其他地方或者其他省份。在历史上的许多时期, 人口迁移是很频繁的, 山西也是如此, 甚至政府有组织的移民行为也是确定的事实, 为什么就不能有洪洞来的移民呢?”在列举了两个迁自山西洪洞“羊獬”村和“柳子沟”村移民的事例后,赵世瑜认为:“问题在于这些在族谱中自称是洪洞移民的数量太大了, 对此, 已有学者表示怀疑, 并认可洪洞作为移民中转站的说法,但这并无可信的史料依据。”
在这一相当委婉的表达后面,我们还是读出了以下几点不信任或不确定:其一,关于族谱记载的可信性;其二,关于是否存在移民中转站;其三,关于政府组织移民之过程。
关于族谱资料是否可靠,在以前有关山东移民的研究中,我曾经将地方志与地名志的记载与《明实录》对勘,证明地方志与地名志资料的可靠性。[4]在山东,1990年代编撰之各县地名志,其实就是族谱关于族源记载之集合,可以当作族谱资料来运用。然而,这一作法并未扩大到淮河以南地区。关于移民中转站,由于“并无可信的史料依据”,所以,也未加以专门的论述。关于政府组织移民之性质,在华北地区,由于《明实录》中存在大量记载,并不成为一个问题。而在淮河以南,由于史料缺乏,明初大移民是否为政府组织也是一个亟待证明的大问题。
鉴于此,本文将首先证明明代初年淮河以南地区移民的性质,即南方地区的移民是中央政府组织的移民;其次,本文将以“瓦屑坝”为例,对“移民中转站”的假说进行验证;最后,本文对于族谱中的“瓦屑坝”及其他移民原籍,给予新的假设与证明。
|
|
|